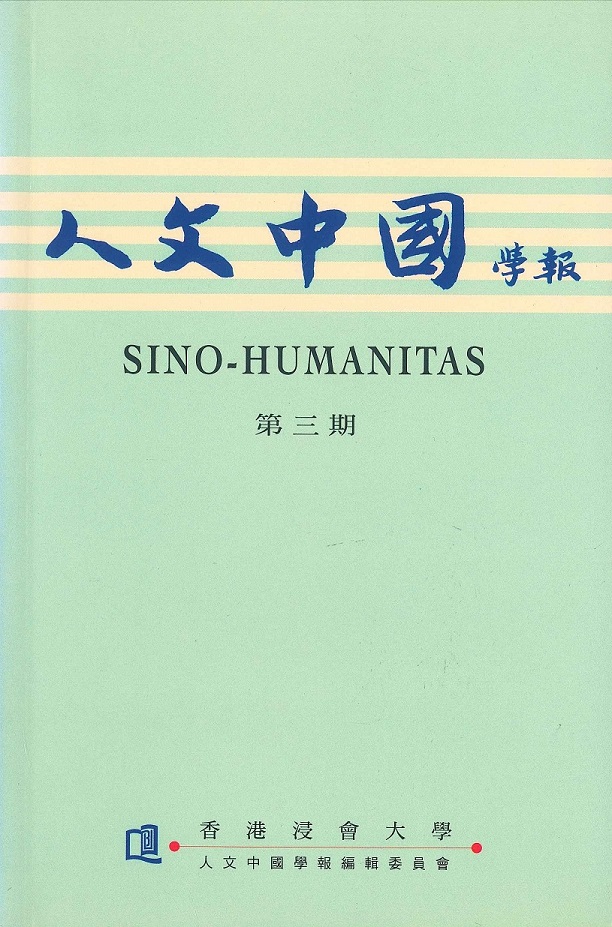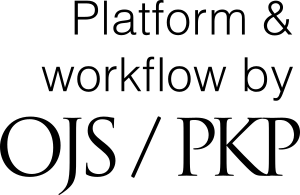鄕音已改——自由民教育的比較觀
DOI:
https://doi.org/10.24112/sinohumanitas.32310Abstract
LANGUAGE NOTE | Document text in Chinese only.
謝校長、施熙柏(Hiebert)院長、各位教授同仁、同學和全體貴賓:浸會大學在香港作育英才無數,今天下午我能在此演講,恭賀貴校四十周年校慶,深感殊榮。貴校從海外遴選來此共襄盛會的客人才不過數位,區區竟叨忝其間,又令我倍感光采。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倘能容我説得切身一些,這點令我感激尤甚的是,今年也是我離港四十周年:就在貴校草創當年,我揮別九龍塘故居(講得精確點,是約道九號),揚帆赴美接受大學及研究院教育。縱然我要到此刻才有幸站在會大學的講台上,我要説若非責校盛情邀請,我還不能深刻感受到遊子返鄉的喜悦。
在今天這種舊雨重逢的場合裏,我也很難不提到八世紀的唐代詩人賀知章。他的七言絕句〈回鄉偶書〉,許多中國人可能從小學時代就已經背得滾瓜爛熟,而引用者又代不乏人,縱然有一點陳腔濫調的味道,更早已變成返鄉的渴望與感覺的典型代表。這首詩大家耳熟能詳,一定記得前兩句: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詩中「鄉音」一詞,指的當然是敍述者的言談方式,字面上可能包含所用方言的習語體式和正確聲調。這種語言現象清楚顯示,從中國中世紀——甚或是上古盛世以來——語言上的地域主義早已蔚為風氣。如此理解,賀知章用這兩句詩寫下來的境遇,就不僅止於他個人的生平感懷。數百年來,這兩句詩頻見引用,吟詠背誦,中國人恆古肯定與冀求的言簡意賅的理想合盤托出,我們心領神會。詩中的敍述者如今已「鬢毛衰」,而這種體態上極其私祕的明顯改變顯示時間飛逝,自然或許也因此而變化不迭,敍述者的文化養成——亦即其人的「鄉音」——卻不知怎的仍未改變。換句話説,人類後天所習,不會為生理或遺傳所囿。
我這般解讀〈回鄉偶書〉中的這兩句詩,並不是要暗示賀知章作詩時,心中已存有自然與文化的對立分野。我們都知道,現代教育奠基在西方的人文學科之上,而後者又弁創於五世紀的雅典。上述兩個範疇,正是現代教育的要項。現代人認為,語言乃話語的某種形式,不是與生俱來,而是下過工夫才能習 得。此一見解,賀知章甚且大有可能不知。然而我真正想説是,從現代人的角度來閲讀這首唐詩——即如我目前所致力者——實不能置其諷意於不顧。詩人所説都關乎自己,這一點真而又真,不用質疑可也。儘管如此,由於此刻我正在挪用這兩行以説明我目前的心境,所以我還是不能不問個問題:賀知章的説法,有多少適用於像我一樣的讀者?
至少就我個人而言,賀知章詩中所説和我的情況有異。這一點我心知肚明。一九五六年離開香港以來,我雖曾數度返港,卻越來越覺得「鄉音」已經逐漸在轉變。我當然沒有忘記廣東話,每天家裏都還在説。在學校,也常和廣東來的學生説。遇有親戚來訪,那甭提講的一定是廣東話。雖然如此,幾年來,耳朵尖的香港朋友和親人卻也常賜教,從我日常所講中發現發音怪奇,偶爾會竄改句構,字彙也用得頗為造作。廣東話的生命日新月異,全仗無以數計新鑄的字詞所致,而友人或親戚更不斷笑話我孤陋寡聞,這方面一概懵懂無知。易言之,我的返鄉避免不了、也掩飾不了我「鄉音已改」的明顯事實。這個名詞待會兒會是演講的主要隱喻,我認為所指不限於話語型態和習慣的變革。過去四十年來,我在海外從學生當起,以迄目前忝列大學教席,如果説我在其他方面一無更改,那是自欺欺人。我改變的可多了,包括知識、學術觀念、感情上的偏愛,以及價值觀等等。總而言之,這也就説我整個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都已不同於往昔。我惟有敞開心胸,招認自己的轉變,才能抖膽一談「自由民」或「文理」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這個課題,因為這個課題本身早已貼上「鄉音已改」的標籤。
Published
How to Cite
Issue
Section
License
Copyright (c) 1996 人文中國學報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The CC BY-NC 4.0 license permits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nd not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Copyright on any article is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 the publisher(s).